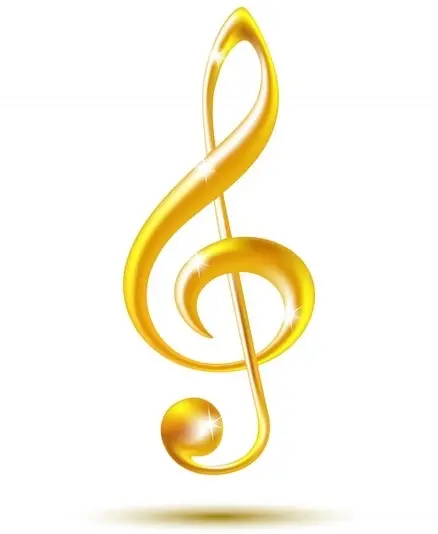
調性 |
法語 tonalite,德語。 Tonalitat,也Tonart
1) 模式的高度位置(由 IV Sposobina 確定,1951,基於 BL Yavorsky 的想法;例如,在 C-dur “C”中是模式主音高度的指定,和“dur”——“major”——模式特徵)。
2)分層。 功能差異化高度連接的集中式系統; T. 在這個意義上是調式和實際 T. 的統一,即調性(假設 T. 定位在某個高度,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即使沒有這種本地化,也可以理解該術語,完全符合mode的概念,尤其是國外lit-re)。 在這個意義上,T. 也是古代獨奏曲(參見:Lbs J., “Tonalnosc melodii gregorianskich”, 1965)和 20 世紀音樂所固有的。 (參見,例如:Rufer J.,“Die Zwölftonreihe:Träger einer neuen Tonalität”,1951 年)。
3)以更窄、更具體的方式。 T. 的含義是功能差異化的音高連接系統,在輔音三元組的基礎上分層集中。 T. 在這個意義上與古典浪漫主義的“和聲調性”特徵相同。 17-19世紀的和聲系統; 在這種情況下,存在許多 T. 和定義。 它們相互關聯的系統(T 系統;參見五度圈、鍵的關係)。
簡稱“T”。 (在狹義的、特定的意義上)調式——大調和小調——可以被想像為與其他調式(愛奧尼亞調式、伊奧利亞調式、弗里吉亞調式、日常調式、五聲調式等)處於同等地位; 事實上,它們之間的區別是如此之大,以至於用術語來說是非常合理的。 大調和小調的對立是和聲。 單音調。 煩惱。 不同於單體。 煩惱,大調和小調 T .. 是分機固有的。 活力和活動,有目的運動的強度,最大程度合理調整的集中度和功能關係的豐富性。 根據這些屬性,音調(與單調調式不同)的特點是對調式中心的清晰和持續的吸引力(“遠距離作用”,SI Taneev;主音在不發聲的地方占主導地位); 局部中心(步驟、功能)的定期(公制)變化,不僅沒有取消中心引力,而且最大限度地實現和強化它; 辯證的是鄰接和不穩定之間的比例(特別是,例如在單個系統的框架內,在I中具有VII度的一般引力,I度的聲音可能被吸引到VII)。 由於對諧波系統中心的強大吸引力。 T.,可以說,吸收了其他模式作為步驟,“內部模式”(BV Asafiev,“作為過程的音樂形式”,1963 年,第 346 頁;步驟 – 多里安,前弗里吉亞模式,作為弗里吉亞語的主要補品turn 成為和聲小調的一部分,等等)。 因此,大調和小調概括了歷史上先於它們的調式,同時體現了調式組織的新原則。 音調系統的活力與現代歐洲思想的本質(特別是啟蒙運動的思想)有間接聯繫。 “實際上,情態代表了一種穩定的世界觀,調性代表了一種動態的世界觀”(E. Lovinsky)。
在 T. 系統中,一個單獨的 T. 獲得一個確定的。 在動態諧波中起作用。 和調色師。 關係; 此功能與關於音調的特徵和顏色的廣泛觀念有關。 於是,C-dur這個系統中的“中心”基調,就顯得更加“簡單”、“白”了。 音樂家,包括主要的作曲家,往往都有所謂的。 顏色聽力(對於 NA Rimsky-Korsakov,顏色 T.E-dur 是亮綠色,田園,春天白樺樹的顏色,Es-dur 是黑暗,陰沉,灰藍色,“城市”和“堡壘”的基調; L Beethoven 稱 h-moll 為“黑色調性”),因此這個或那個 T. 有時與定義相關聯。 會表達。 音樂的性質(例如,WA 莫扎特的 D-dur、貝多芬的 c-moll、As-dur),以及產品的換位。 – 隨著風格的變化(例如,莫扎特的經文歌 Ave verum 語料庫,K.-V. 618,D-dur,在 F. Liszt 的改編中轉移到 H-dur,從而經歷了“浪漫化”)。
在古典大調-小調 T 占主導地位的時代之後,“T”的概念出現了。 也與分支音樂邏輯的想法有關。 結構,即關於任何音高關係系統中的一種“順序原則”。 最複雜的音調結構成為(從 17 世紀開始)一種重要的、相對自主的音樂手段。 表現力和音調戲劇有時會與文本、舞台、主題競爭。 就像 int 一樣。 T. 的生命表現在和弦的變化中(步進、功能——一種“微型小伙子”),一個完整的音調結構,體現了最高水平的和聲,生活在有目的的調製動作中,T 變化。 因此,整體的調性結構成為發展音樂思想中最重要的要素之一。 “讓旋律模式被更好地破壞,”PI 柴可夫斯基寫道,“而不是直接依賴於調製與和聲的音樂思想的本質。” 在發達的音調結構中。 T. 可以起到類似於主題的作用(例如,普羅科菲耶夫第七鋼琴奏鳴曲終曲第二主題的e-moll作為奏鳴曲第二樂章E-dur的反映創造了一個準-主題語調“arch”-在整個週期的音階上回憶)。
T. 在繆斯的構建中的作用異常巨大。 形式,尤其是大的形式(奏鳴曲、迴旋曲、循環曲、大型歌劇):“持續停留在一個調上,反對或多或少快速變化的轉調,對比音階的並置,逐漸或突然過渡到一個新調,準備返回到主要部分”,——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將浮雕和凸起傳達給作品的大部分,並使聽眾更容易感知它的形式”(SI Taneev;見音樂形式)。
在其他和聲中重複動機的可能性導致了新的、動態的主題形成; 重複主題的可能性。 其他 T. 中的編隊使得有機發展大型繆斯成為可能。 形式。 相同的動機元素可以呈現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含義,這取決於音調結構的差異(例如,在音調變化的條件下,延長的碎片會產生加劇發展的效果,而在主音的條件下主調,相反,“凝”的作用,停止發展)。 在歌劇形式中,T.的變化往往等於情節情境的變化。 只有一個色調計劃可以成為一層繆斯。 形式,例如。 T. 在第一天的變化。 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
古典純正和成熟的音調外觀(即“和諧音調”)是維也納古典音樂和與其時間順序接近的作曲家(最重要的是 17 世紀中葉和 19 世紀中葉的時代)的音樂特徵世紀)。 然而,和聲 T. 出現得更早,並且在 20 世紀的音樂中也很普遍。 T. 的準確時間界限作為一個特殊的、特定的。 由於分解,很難確定品格的形式。 可以作為依據。 複合體的特點: A. Mashabe 約會諧波的出現。 T. 14 世紀,G. Besseler – 15 世紀,E. Lovinsky – 16 世紀,M. Bukofzer – 17 世紀。 (參見 Dahhaus S.,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harmonischen Tonalität,1); IF 斯特拉文斯基將 T. 的主導地位指的是從中間開始的時期。 1968 年至 Ser。 17 世紀 Complex Ch. 經典(和聲)T. 的符號:a) T. 的中心是輔音三元組(此外,可以想像為一個整體,而不是音程的組合); b) 調式——大調或小調,由和弦系統和“沿著這些和弦的畫布”移動的旋律表示; c) 基於 19 個功能(T、D 和 S)的品格結構; “特徵不協和音”(S 與六度音,D 與七度音;術語 X. 黎曼); T是諧音; d) T.內部和聲的變化,直接感覺傾向於補品; e) 一個韻律系統和韻律之外的和弦四五音關係(好像從韻律轉移並擴展到所有連接;因此術語“韻律 t”),分層。 和聲的分級(和弦和調); f) 非常明顯的韻律外推(“音調節奏”),以及一種形式——一種基於方形和相互依存的“押韻”節奏的結構; g) 基於調製的大型形式(即改變 T.)。
這種系統的主導地位出現在 17-19 世紀,當時 Ch 的複雜性。 通常,T. 的跡像是完整的。 即使在 otd 中也觀察到符號的部分組合,這給人以 T 的感覺(與模態相對)。 文藝復興時期(14-16 世紀)的著作。
在 G. de Macho(他也創作了單聲道音樂作品)中,在其中一首 le(No 12;“Le on death”)中,“Dolans cuer las”部分是以主調為主的大調寫成的。 整個音高結構的三元組:
G. de Macho。 第 12 曲,第 37-44 小節。
作品節選中的“Monodic major”。 Masho 仍然遠非經典。 類型 T.,儘管有許多符號的巧合(在上述符號中,出現了 b、d、e、f)。 通道。 不同之處在於單音倉庫並不意味著諧音伴奏。 複調音樂中功能性節奏的最早表現之一是 G. Dufay 的歌曲(迴旋曲)“Helas, mad dame”(根據 Besseler 的說法,“它的和聲似乎來自一個新世界”):
G. 杜菲。 迴旋曲“Helas, ma dame par amours”。
和諧的印象。 T. 是計量函數偏移和諧波占主導地位的結果。 四分之一比例的化合物,諧波中的 T – D 和 D – T。 整體的結構。 同時,系統的中心與其說是三和弦(儘管它偶爾會出現,例如第 29、30 小節),而是五度音(允許大三度和小三度,而沒有故意混合大小調模式的效果) ; 模式比和弦更旋律(和弦不是系統的基礎),節奏(沒有度量外推)不是調性的,而是模態的(五小節沒有任何方向的方形); 沿著結構的邊緣音調重力是明顯的,而不是完全的(人聲部分根本不是從主音開始的); 沒有音調功能層次,也沒有協和不協和與和聲的調性意義的聯繫; 在節奏的分佈中,對主導的偏見是不成比例的。 總的來說,即使這些作為特殊類型的語氣系統的清晰的聲調符號仍然不允許我們將這些結構歸因於聲調本身; 這是 15 至 16 世紀的典型模態(從廣義上的 T. 的角度來看 – “模態調性”),在其框架內,獨立的部分成熟。 T. 的組成部分(參見 Dahinaus C,1968,第 74-77 頁)。 教堂的倒塌在一些音樂中令人煩惱。 產品。 騙局。 16 – 乞求。 17 世紀創造了一種特殊類型的“自由 T”。 – 不再是調式的,但還不是古典的(N. Vicentino 的經文歌,Luca Marenzio 和 C. Gesualdo 的牧歌,G. Valentini 的等音奏鳴曲;參見下面第 567 欄中的示例)。
缺乏穩定的調式音階和相應的旋律。 公式不允許將此類結構歸因於教堂。 煩惱。
C. 熱蘇阿爾多。 牧歌“Merce!”。
存在一定的節奏,中心。 和弦——一個輔音三和弦,“和聲音階”的變化使我們有理由認為這是一種特殊類型的 T。——半音調 T。
大調-小調節奏的主導地位逐漸確立於 17 世紀,主要出現在舞蹈、日常和世俗音樂中。
然而,古老的教堂煩惱在一樓的音樂中無處不在。 以 1 世紀為例。 J. Frescobaldi (Ricercare sopra Mi, Re, Fa, Mi – Terzo tuono, Canzona – Sesto tuono。Ausgewählte Orgelwerke, Bd II, No 17, 7), S. Scheidt (Kyrie dominicale IV. Toni cum Gloria, Magnificats, 見 Tabuiatura nova, III.pars). 甚至 JS Bach,他的音樂以發達的口琴為主。 T.,例如,這種現象並不少見。 讚美詩
J. 道蘭。 牧歌《醒了,愛!》 (1597)。
Aus tiefer Not schrei' ich zu dir and Erbarm' dich mein, O Herre Gott (after Schmieder Nos. 38.6 and 305; Phrygian mode), Mit Fried' und Freud'ich fahr' dahin (382, 多里安), Komm, Gott Schöpfer , heiliger Geist (370; Mixolydian)。
主要-次要類型的嚴格功能音色發展的頂峰落在維也納古典時代。 這個時期的主要和諧規律被認為是一般和諧的主要屬性; 它們構成了所有和聲教科書的主要內容(參見和聲、和聲函數)。
T.的發展在二樓。 2 世紀包括擴大 T 的限制(混合大調-小調,進一步的半音階系統),豐富音調-功能關係,極化全音階。 和彩色。 和諧,色彩的放大。 t.的含義,在新的基礎上復興調式和聲(主要與民間傳說對作曲家作品的影響有關,特別是在新的民族學校中,例如俄語),自然調式的使用,以及作為“人工”對稱的(參見 Sposobin I V.,“關於和諧進程的講座”,19 年)。 這些和其他新功能顯示了 t 的快速發展。 t 的新屬性的綜合效果。 類型(在 F.李斯特、R.瓦格納、MP Mussorgsky、NA Rimsky-Korsakov 中)從嚴格 T. 的角度來看似乎是對它的拒絕。 例如,討論是由瓦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的介紹引起的,其中最初的主音被長時間的延遲所掩蓋,結果出現了關於劇中完全沒有主音的錯誤觀點(“完全迴避”的補品”;參見 Kurt E.,“瓦格納的“特里斯坦”中的浪漫和諧及其危機,M.,1969 年,第 1975 頁;這也是他將初始部分的和聲結構誤解為廣義理解的原因“主導樂觀”,第 305 頁,而不是作為規範說明。,以及對初始部分邊界的錯誤定義——第 299-1 小節而不是第 15-1 小節)。 Symptomatic 是李斯特晚期戲劇之一的名字 – Bagatelle Without Tonality (17)。
T. 新屬性的出現,使其遠離經典。 鍵入,到開頭。 20 世紀導致了系統的深刻變化,許多人將其視為 t.、“無調性”的分解、破壞。 SI Taneyev(在 1906 年完成的“嚴格寫作的移動對位法”中)指出了新音調系統的開始。
T. 的意思是一個嚴格的功能性大調-小調系統,Taneyev 寫道:“在取代了教堂模式之後,我們的音調系統現在反過來退化為一個新系統,它試圖破壞音調並取代和聲的全音階基礎與半音階的,音調的破壞導致音樂形式的分解”(同上,莫斯科,1959 年,第 9 頁)。
隨後,“新系統”(但對塔涅耶夫而言)被稱為“新技術”一詞。 它與經典 T 的基本相似之處在於“新 T”。 也是有層次的。 功能差異化的高空連接系統,體現了邏輯。 音調結構中的連通性。 與舊調性不同的是,新調性不僅可以依靠輔音主音,還可以依靠任何方便選擇的音組,而不僅僅是全音階。 基礎,但廣泛使用功能獨立的 12 種聲音中任何一種的和聲(混合所有模式會產生多模式或“無品”——“新的、非模態 T”;參見 Nü11 E. von,“B . Bartok, Ein Beitrag zur Morphologie der neuen Musik”, 1930); 聲音和輔音的語義可以以新的方式代表經典。 公式 TSDT,但可能會以其他方式披露。 生物。 不同之處還在於,嚴格的古典T.在結構上是統一的,而新T.是個性化的,因此不具有單一的聲音元素複合體,即不具有功能統一性。 因此,在一篇或另一篇文章中,使用了不同的 T 符號組合。
在生產後期的創造力 T. 斯克里亞賓保留其結構功能,但傳統。 和聲被創建特殊模式(“Scriabin 模式”)的新和諧所取代。 因此,例如,在“普羅米修斯”中心。 和弦——著名的“普羅米修斯”六音與 osn。 調 Fis(下例 A),居中。 sphere (“main T.”) – 低頻系列中的 4 個這樣的六音(簡化模式;示例 B); 調製方案(在連接部分 - 示例 C),說明的音調計劃 - 示例 D(“普羅米修斯”的和聲計劃雖然不完全準確,但由作曲家在盧斯部分確定):
新劇院的原則構成了伯格歌劇沃采克 (1921) 的基礎,該歌劇通常被視為“諾文斯基無調性風格”的典範,儘管作者強烈反對“撒旦”一詞“無調性”。 進補有不單單。 歌劇編號(例如,第 2 天的第 1 場 - “eis”;從第 3 天的第 1 場進行曲 - “C”,他的三重奏 - “As”;第 4 天第 2 場跳舞 - “ g”,瑪麗被謀殺的場景,第二天的第二個場景 – 中心音“H”等)和整個歌劇(主音“g”的和弦),但更多不僅如此——在所有生產中。 “leit heights”的原則一直得到執行(在 leit tonalities 的背景下)。 是的,通道。 英雄有輕音“Cis”(第 2 節,第 2 小節——名字“Wozzeck”的第一個發音;進一步的小節 1-5,士兵 Wozzeck 的話“沒錯,上尉先生”;小節 87- 89 – Wozzeck 的詠嘆調“我們可憐的人!”,在 136d 小節 153-3 中——cis-moll 三和弦在第 220 場景的主和弦中“閃耀”)。 如果不考慮調性戲劇,就無法理解歌劇的一些基本思想; 因此,歌劇最後一幕(沃采克死後,第 319 節,第 4-3 小節)中兒童歌曲的悲劇在於,這首歌的音調是 eis(moll),即沃采克的 leitton; 這揭示了作曲家認為無憂無慮的孩子是小“wozzets”的想法。 (參見 König W.,Alban Bergs Oper“Wozzeck”中的 Tona-litätsstrukturen,372 年。)
dodecaphonic-serial 技術引入獨立於音調的結構連貫性,同樣可以利用音調的效果,也可以不用它。 與流行的誤解相反,十二音很容易與(新)T 的原理和中心的存在相結合。 色調是它的典型屬性。 12 音系列的想法最初是作為一種能夠補償主音和 t 失去的建設性效果的手段而產生的。 協奏曲、奏鳴曲循環)。 如果連續生產是在音調模型上進行的,那麼基礎、補品、音調領域的功能可以通過特定的系列來執行。 音高,或特別分配的參考聲音、音程、和弦。 “原始形式的行現在起著與過去演奏的“基本鍵”相同的作用; “重演”自然會回到他身上。 我們節奏相同! 這種與早期結構原則的類比是有意識地保持的(……)”(Webern A.,音樂講座,1975 年,第 79 頁)。 例如,AA Babadzhanyan 的戲劇“Choral”(來自“Six Pictures”的鋼琴曲)是用一個“主 T”寫成的。 中心為 d(和輕微著色)。 RK Shchedrin 在 12 音主題上的賦格有一個清晰表達的 T. a-moll。 有時高度關係很難區分。
A.韋伯恩。 音樂會作品。 24.
因此,在協奏曲中使用系列的親和力。 24(有關係列,請參見 Art.Dodecaphony),Webern 收到一組特定的三音。 高度,重返克里米亞被視為回歸“主鍵”。 下面的示例顯示了主音的三個聲音。 球體 (A)、第一樂章的開頭 (B) 和韋伯恩協奏曲終曲的結尾 (C)。
然而,對於 12 音音樂,這種“單音”作曲原則是沒有必要的(如在古典調性音樂中)。 儘管如此,T. 的某些組件,即使是新形式,也經常被使用。 因此,EV Denisov (1971) 的大提琴奏鳴曲有一個中心音“d”,AG Schnittke 的系列第二小提琴協奏曲有主音“g”。 在 2 年代的音樂中。 70世紀有加強新T原則的傾向。
關於 T. 的教義歷史植根於教會的理論。 模式(參見中世紀模式)。 在其框架內,關於韻母的想法被發展為調式的一種“補品”。 “調式”(mode)本身,從廣義的角度來看,可以認為是T的一種形式(types)。引入調式(musica ficta,musica falsa)的做法為tone的出現創造了條件旋律效果。 和對主音的和弦引力。 從句理論在歷史上為“聲調抑揚頓挫”理論奠定了基礎。 Glarean 在他的 Dodecachord (1547) 中從理論上使很久以前就存在的 Ionian 和 Aeolian 調式合法化,其音階與大調和自然小調一致。 J. Tsarlino (“The Doctrine of Harmony”, 1558) 基於中世紀。 比例學說將輔音三元組解釋為單位,並創造了大調和小調理論; 他還注意到所有模式的主要或次要特徵。 1615年,荷蘭人S.德科(de Caus)更名為反響堂。 音調成為主導(在真實模式中 - 五度,在 plagal - IV)。 I. Rosenmuller 寫了大約。 1650 年大約只存在三種調式——大調、小調和弗里吉亞調。 在 70 年代。 17世紀的NP Diletsky將“musicia”分為“funny”(即大調)、“pitiful”(小調)和“mixed”。 1694 年,Charles Masson 只發現了兩種模式(Mode majeur 和 Mode mineur); 在每個步驟中,有 3 個步驟是“必不可少的”(Finale、Mediante、Dominante)。 在 S. de Brossard(1703 年)的“音樂詞典”中,品格出現在 12 個半音半音中的每一個上。 伽馬。 t的基本學說。 (沒有這個詞)是由 JF Rameau (“Traité de l'harmonie …”, 1722, “Nouveau systéme de musique théorique”, 1726) 創造的。 品格是建立在和弦(而不是音階)的基礎上的。 Rameau 將模式描述為由三重比例決定的連續順序,即三個主和弦的比例 - T、D 和 S。和 S,解釋了主音在模式的所有和弦上的主導地位。
術語“T”。 首次出現在 FAJ Castile-Blaz (1821)。 T. – “音樂調式的屬性,在其基本步驟的使用中表現(存在)”(即 I、IV 和 V); FJ Fetis (1844) 提出了 4 種類型的 T 的理論:單調性 (ordre unito-nique)——若積。 它是用一個鍵寫的,沒有轉調成其他鍵(對應於 16 世紀的音樂); 過渡性——轉調用於近音(顯然是巴洛克音樂); 多音性——轉調用於遠音、不和聲(維也納古典時代); omnitonality (“all-tonality”) – 不同鍵的元素的混合,每個和弦都可以跟隨每個(浪漫主義時代)。 然而,不能說 Fetis 的類型學是有根據的。 X. Riemann (1893) 創立了嚴格的音色函數理論。 像拉莫一樣,他從和弦的範疇出發,將其作為系統的中心,並試圖通過聲音和輔音的關係來解釋調性。 與 Rameau 不同,Riemann 並沒有簡單地基於 T.3 ch。 和弦,但將其餘部分簡化為它們(“唯一本質的和聲”)(也就是說,在 T 中,黎曼只有對應於 3 個函數的 3 個基 - T、D 和 S;因此,只有黎曼系統是嚴格函數的) . G. Schenker (1906, 1935) 證實音調是一種自然法則,由聲音材料的歷史非演化特性決定。 T. 基於輔音三元組、全音階和輔音對位法(如對位法)。 根據 Schenker 的說法,現代音樂是產生調性的自然潛能的退化和衰退。 勳伯格(1911)詳細研究了現代資源。 諧音給他。 系統而得出的結論是現代的。 調性音樂是“在 T 的邊界”。 (基於對 T. 的舊理解)。 他稱(沒有精確定義)音調的新“狀態”(c. 1900–1910;由 M. Reger、G. Mahler、Schoenberg 所著)術語為“浮動”音調(schwebende;補品很少出現,避免使用足夠清晰的音調)。 ; 例如,勳伯格的歌曲“誘惑”op。 6, No 7) 和“withdrawn” T. (aufgehobene; 避免主音和輔音三和弦,使用“遊走和弦”——聰明的七和弦,增加的三和弦,其他音調的多重和弦)。
黎曼的學生 G. Erpf (1927) 試圖從嚴格的功能理論的角度來解釋 10 年代和 20 年代的音樂現象,並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音樂現象。 埃爾普夫還提出了“輔音中心”(Klangzentrum)或“音中心”的概念(如勳伯格的戲劇op.19 No.6),這對新聲理論具有重要意義; 具有這樣一個中心的 T. 有時也稱為 Kerntonalität (“core-T.”)。 韋伯恩(ch. arr. 從古典 t. 的角度來看)將“古典之後”的音樂發展描述為“t 的毀滅”。 (Webern A.,音樂講座,第 44 頁); T的本質。他決定了踪跡。 方式:“依賴主調”、“塑造手段”、“傳播手段”(同上,第51頁)。 T. 被全音階的“分叉”摧毀了。 步驟(第 53、66 頁),“聲音資源的擴展”(第 50 頁),音調歧義的傳播,回歸主音的需求消失。 音調,傾向於不重複的音調(第 55、74-75 頁),沒有古典的塑造。 成語 T.(第 71-74 頁)。 P. Hindemith (1937) 基於 12 步(“系列 I”,例如,在系統中
他們每個人出現任何不和諧的可能性。 欣德米特對T.元素的價值觀體系非常差異化。 根據 Hindemith 的說法,所有音樂都是調性的; 避免音調交流就像地球引力一樣困難。 IF 斯特拉文斯基對調性的看法很奇特。 考慮到音調(狹義)和諧,他寫道:“和諧……有一段輝煌而短暫的歷史”(“對話”,1971 年,第 237 頁); “我們不再處於學校意義上的經典 T 的框架內”(“音樂詩學”,1949 年,第 26 頁)。 斯特拉文斯基堅持“新 T”。 (“非調性”音樂是調性的,“但不是在 18 世紀的調性系統中”;“對話”,第 245 頁)其中一種變體,他稱之為“聲音、音程甚至聲音複合體”; “音調(或聲音 - “tonale”)極點是......音樂的主軸,”T. 只是“一種根據這些極點定位音樂的方式。” 然而,“極點”這個詞是不准確的,因為它也意味著“相反的極點”,而斯特拉文斯基並不是這個意思。 J. Rufer根據新維也納學派的思想提出了“新調”一詞,認為它是12音系列的承載者。 X. Lang 的論文““調性”概念和術語的歷史”(“Begriffsgeschichte des Terminus “Tonalität””,1956 年)包含有關調性主義歷史的基本信息。
在俄羅斯,音調理論最初是根據“音調”一詞發展起來的(VF Odoevsky,給出版商的信,1863 年;GA Laroche,Glinka 及其在音樂史上的意義,俄羅斯公報,1867-68 年;PI Tchaikovsky , “和聲實用研究指南”,1872 年),“系統”(德語 Tonart,由 AS Famintsyn 翻譯,EF Richter 著“和聲教科書”,1868 年;HA Rimsky -Korsakov,“和聲教科書”,1884-85 ), “mode” (Odoevsky, ibid; Tchaikovsky, ibid), “view” (來自 Ton-art, AB Marx's Universal Textbook of Music, 1872 的 Famintsyn 翻譯)。 柴可夫斯基的“和聲簡明手冊”(1875 年)大量使用了術語“T”。 (偶爾也出現在和諧實踐研究指南中)。 SI Taneyev 提出了“統一調性”的理論(參見他的著作:“Analysis of modulation plans …”,1927;例如,G-dur 中的連續偏差,A-dur 喚起了 T.D 的想法-dur,將它們結合起來,並對其產生音調吸引力)。 與西方一樣,在俄羅斯,調性領域的新現象最初被視為缺乏“調性統一”(Laroche,同上)或調性(Taneyev,6 年 1880 月 12 日給柴可夫斯基的信),因此“在系統的限制之外”(里姆斯基-科薩科夫,同上)。 Yavorsky 描述了與新音調(沒有這個術語)相關的許多現象(1908 半音系統、不協和和分散的主音、音調中模態結構的多樣性,以及大多數模式在大調和小調之外); 在 Yavorsky Russian 的影響下。 例如,理論音樂學試圖尋找新的模式(新的高海拔結構)。 在創作晚期斯克里亞賓的作品中(BL Yavorsky,“音樂演講的結構”,1911 年;“與李斯特紀念日有關的一些想法”,1930 年;Protopopov SV,“音樂演講結構的要素” , 1963) 印象派, – 寫了 BV Asafiev, – 沒有超越音調和聲系統的限制”(“音樂形式作為一個過程”, M., 99, p. 60). GL Catuar(繼 PO Gewart 之後)開發了所謂的類型。 擴展 T.(主要-次要和半音階系統)。 BV Asafiev 從語調理論的角度分析了聲調現象(聲調、D 和 S 的作用、“歐洲調式”的結構、介紹聲、聲調元素的文體解釋) . 於。 N. Tyulin 對變量思想的發展極大地補充了音調函數的理論。 70-12 年代的一些貓頭鷹音樂學家(MM Skorik、SM Slonimsky、ME Tarakanov、HP Tiftikidi、LA Karklinsh 等)。 詳細研究了現代的結構。 1972 步(半音階)音調。 塔拉卡諾夫特別提出了“新 T”的想法(參見他的文章:“XNUMX 世紀音樂中的新調性”,XNUMX)。
參考文獻: Nikolai Diletsky 的《音樂家語法》(編) C. 在。 斯摩棱斯基),聖。 聖彼得堡,1910 年,再版。 (訂單中。 在。 在。 Protopopova), M., 1979; (奧多耶夫斯基 V. F.),五世親王的來信。 P. 奧多耶夫斯基 (Odoevsky) 向出版商介紹原始的偉大俄羅斯音樂,合集:Kaliki passable?,第 XNUMX 部分。 2號 5,M.,1863 年,同上,在書中:Odoevsky V. F. 音樂和文學遺產,M.,1956 年; 拉羅什 G. A.,格林卡及其在音樂史上的意義,《俄羅斯信使》,1867年,第10期,1868年,第1期,第9-10期,同,在書中:Laroche G. A.,精選文章,卷。 1, L., 1974; 柴可夫斯基 P. I.,和諧實踐研究指南,M.,1872 年; 里姆斯基-科薩科夫 N. A.,和諧教科書,沒有。 1-2,聖。 聖彼得堡,1884-85 年; 亞沃爾斯基 B. L.,音樂演講的結構,部分。 1-3,M.,1908 年; 他的,關於 P 週年紀念日的一些想法。 李斯特,“音樂”,1911 年,第 45 號; 塔內耶夫 S. I.,嚴格寫作的可移動對位法,萊比錫,1909 年,M.,1959 年; Belyaev V.,“貝多芬奏鳴曲中轉調的分析”S. 和。 Taneeva,在書中:關於貝多芬的俄文書籍,M.,1927 年; 塔內耶夫 S. I., 給 P 的信 和。 柴可夫斯基日期為 6 年 1880 月 XNUMX 日,在書中:P. 和。 柴可夫斯基。 C. 和。 塔內耶夫。 Letters, M., 1951; 他的,關於音樂理論問題的幾封信,在書中:S. 和。 塔內耶夫。 材料和文件等 1、莫斯科,1952; 阿夫拉莫夫 A. M.,“Ultrachromatism”還是“omnitonality”?,“Musical Contemporary”,1916 年,書籍。 4-5; 羅斯拉維茨 N. A.,關於我自己和我的作品,《現代音樂》,1924年,第5期; Cathar G. L.,和諧的理論課程,部分。 1-2,M.,1924-25; 羅索諾夫 E. K.,關於音調系統的擴展和轉變,載於:音樂聲學委員會作品集,卷。 1, M., 1925; 風險 P。 A.,調性的終結,現代音樂,1926 年,第 15-16 號; 普羅托波夫 S. 五,音樂演講的結構要素,部分。 1-2,M.,1930-31; 阿薩菲耶夫 B. 五,音樂形式作為一個過程,書。 1-2,M.,1930-47,(兩本書合在一起),L.,1971 年; Mazel L.,Ryzhkin I.,理論音樂學史論文集,卷。 1-2,M.-L.,1934-39; 秋林玉。 H.,關於和諧的教學,L.,1937 年,M.,1966 年; Ogolevets A.,現代音樂思想導論,M.,1946 年; Sposobin I。 V., 音樂基礎理論, M., 1951; 他自己的,關於和諧進程的講座,M.,1969 年; 斯洛尼姆斯基 C. M.,普羅科菲耶夫的交響曲,M.-L.,1964 年; 斯克列布科夫 C. S.,如何解釋調性?,“SM”,1965 年,第 2 期; 蒂夫提基迪 H. P.,半音階系統,載於:音樂學,卷。 3, A.-A., 1967; Tarakanov M.,普羅科菲耶夫交響曲風格,M.,1968 年; 他的,二十世紀音樂的新調性,收藏:音樂科學問題,卷。 1、莫斯科,1972; Skorik M., Ladovaya 系統 S. 普羅科菲耶娃,K.,1969 年; 卡克林什 L. A., 和諧 H. Ya Myaskovsky, M., 1971; 馬澤爾 L. A.,古典和聲的問題,M.,1972 年; Dyachkova L.,關於斯特拉文斯基調和系統(極系統)的主要原理,在書中:I。 P. 斯特拉文斯基。 文章和材料,M.,1973; 穆勒 T. F., Harmoniya, M., 1976; Zarlino G., Le istitutioni harmonice, Venetia, 1558(傳真:傳真中的音樂和音樂文學紀念碑,第二系列,N. Y.,1965); Сaus S. de,諧波研究所……,法蘭克福,1615 年; 拉莫·J。 Ph., Treaty of harmony..., R., 1722; его же, 新的理論音樂體系......, R., 1726; Castil-Blaze F. H. J.,現代音樂詞典,c。 1-2, R., 1821; Fétis F. J., Trait© complet de la theory…, R., 1844; 黎曼 H., Einfachte Harmonielehre…, L.-N. Y., 1893 (俄語。 每。 – Riman G., Simplified harmony?, M., 1896, 同上, 1901); 他自己的,Geschichte der Musiktheorie…, Lpz., 1898; 他自己的,bber Tonalität,在他的書中:Präludien und Studien, Bd 3, Lpz., (1901); 他自己的,Folklonstische Tonalitätsstudien,Lpz.,1916 年; 格瓦特 F. A.,理論和實踐和諧條約,訴。 1-2,R.-Brux.,1905-07,Schenker H.,新音樂理論和幻想......,卷。 1,Stuttg.-B.,1906 年,第一卷。 3, W., 1935; SchönbergA., Harmonielehre, Lpz.-W., 1911; Кurt E.,理論諧波的先決條件……,伯爾尼,1913 年; его же, 浪漫的和諧......, Bern-Lpz., 1920 (рус. 每。 – Kurt E.,瓦格納的浪漫和諧及其危機 Tristan, M., 1975); Hu11 A.,現代和諧……,L.,1914 年; Touzé M., La tonalité chromatique, “RM”, 1922, v. 3; Güldenstein G, Theorie der Tonart, Stuttg., (1927), Basel-Stuttg., 1973; Erpf H.,現代音樂的和聲與聲音技術研究,Lpz.,1927; Steinbauer O.,調性的本質,慕尼黑,1928 年; Cimbro A., Qui voci secolari sulla tonalita, «拉斯。 穆斯。》,1929 年,第 XNUMX 期。 2; Hamburger W.,調性,“序曲”,1930 年,10 年級,H. 1; 尼爾 E. 來自 B Bartok,哈勒,1930 年; Karg-Elert S.,聲音和調性的極化理論(諧波邏輯),Lpz.,1931 年; Yasser I,音調演變理論,N. Y., 1932; 他的,調性的未來,L.,1934 年; 斯特拉文斯基 I., Chroniques de ma vie, P., 1935 (rus. 每。 – Stravinsky I., Chronicle of my life, L., 1963); 他自己的,Poétique musicale,(第戎),1942 年(俄語。 每。 – 斯特拉文斯基 I.,《音樂詩學的思考》,書中:I. F. 斯特拉文斯基。 文章和材料,M.,1973); 斯特拉文斯基對話羅伯特·克拉夫特,L.,1958 (rus. 每。 – Stravinsky I., Dialogues …, L., 1971); Appelbaum W.,Accidentien und Tonalität in den Musikdenkmälern des 15。 16 歲。 世紀, B., 1936 (Diss.); Hindemith P.,作曲指導,卷。 1, 美因茨, 1937; Guryin O., Fre tonalitet til atonalitet, 奧斯陸, 1938; Dankert W.,旋律調性和調性關係,«音樂»,1941/42,卷。 34; 瓦登·J。 L.,早期歐洲音樂的調性方面,Phil.,1947 年; Кatz A.,對音樂傳統的挑戰。 調性的新概念,L.,1947 年; Rohwer J., Tonale Instructions, Tl 1-2, Wolfenbьttel, 1949-51; его ez, 關於調性的本質問題……, «Mf», 1954, vol. 7,H. 2; Вesseler H., Bourdon and Fauxbourdon, Lpz., 1, 1950; Sсhad1974er F.,調性問題,Z.,1(diss.); ADings H., Tonalitcitsproblemen en de nieuwe muziek, Brux., 1950; Rufer J.,十二音系列:新調性的載體,«ЦMz»,1951 年,年。 6,第 6/7 號; Salzer F.,結構聽證會,訴。 1-2,N。 Y., 1952; Machabey A., Geníse de la tonalit© musicale classique, P., 1955; Neumann F.,調性與無調性……,(Landsberg),1955 年; Ва11if C1., Introduction а laйtatonalitй, P., 1956; Lang H.,“調性”一詞的概念史,弗萊堡,1956 年(論文); Reti R.,調性。 無調性。 Pantonality, L., 1958 (rus. 每。 – Reti R.,現代音樂中的調性,L.,1968 年); 特拉維斯 R.,走向新的調性概念?,音樂理論雜誌,1959 年,v。 3、2號; Zipp F., 自然泛音系列和調性是否過時了?, «Musica», 1960, vol. 14,H. 5; Webern A.,新音樂之路,W.,1960 (рус. 每。 – Webern A.,音樂講座,M.,1975 年); Eggebrecht H., Musik als Tonsprache, “AfMw”, 1961, Jahrg. 18,H. 1; Hibberd L., «Tonality» 和相關術語問題, «MR», 1961, v. 22號 1; Lowinsky E.,十六世紀音樂中的調性與無調性,Berk.-Los Ang.,1961 年; Apfe1 E.,作為大調-小調調性基礎的中世紀晚期音樂的調性結構,«Mf»,1962 年,卷。 15,H. 3; 他自己的,Spätmittelalterliche Klangstruktur und Dur-Moll-Tonalität,同上,1963 年,Jahrg。 16,H. 2; Dah1haus C.,新音樂中調性的概念,國會報告,卡塞爾,1962 年; eго же,諧波調性起源的調查,卡塞爾 — (u. a.), 1968; Finscher L.,現代開始時的調性命令,в кн.:當時的音樂問題,卷。 10、卡塞爾,1962; Pfrogner H.,關於我們時代調性的概念,«Musica»,1962 年,卷。 16,H. 4; Reck A.,音調試聽的可能性,«Mf»,1962 年,卷。 15,H. 2; Reichert G.,舊音樂中的基調和調性,в кн.:當時的音樂問題,卷。 10、卡塞爾,1962; Barford Ph., Tonality, «MR», 1963, v. 24 號,第 3 號; Las J.,格里高利旋律的調性,Kr.,1965 年; 桑德斯 E. H.,13 世紀英國複調音樂的調性方面,«音樂學報»,1965 年,v. 37; 恩斯特。 V.,關於調性的概念,國會報告,Lpz.,1966 年; Reinecke H P.,關於調性的概念,там же; Marggraf W.,Machaut 和 Dufay 之間法國香頌的調性與和諧,«AfMw»,1966 年,卷。 23,H. 1; George G.,調性與音樂結構,N. Y.-Wash., 1970; Despic D., Teorija tonaliteta, 貝爾格萊德, 1971; Atcherson W.,17 世紀的基調和調式,《音樂理論雜誌》,1973 年,v. 17號,2號; Кцnig W.,Alban Berg 的歌劇《Wozzeck》中的調性結構,Tutzing,1974 年。
於。 N·霍洛波夫



